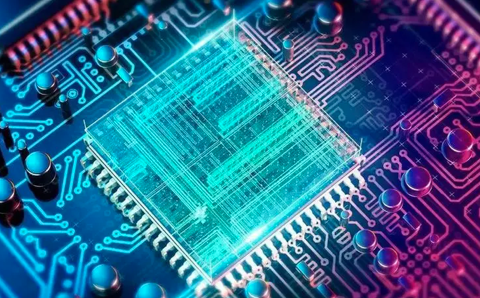【聚焦】电影《敦刻尔克》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每日财讯网》编辑 发布时间:2017-09-22
策划人语:当观众看完一场电影走出影院后,电影给观众留下什么?是对情节的回味?对破解悬念而产生的快感?还是对历史事件重塑之后,引发的长久思考。历史剧、战争片是人类电影史上不可抹去的光辉一笔,利用光影效果重现历史与战争的瞬间,是后辈人感受前人经历,体会当下生活的重要方式。而英雄主义、暴力美学等因素的掺入,使得以往的历史、战争题材影片呈现出诸多有异于史实的面貌。敦刻尔克撤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可忘却的重要事件,诺兰指导的影片《敦刻尔克》却使用了异乎寻常的电影语言,以士兵是否能得以求生为悬念,以幸存为主题,凸显出在历史洪流中,每个个体命运的多变,每个心灵深处的触碰。在光与影之中,个体命运的背后,就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奋发求生,坚持不懈的生动诠释。本刊特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陈瑜博士和珠海行政学院副教授孙莹博士,与读者分享观看影片《敦刻尔克》的思考。
陈瑜:《敦刻尔克》重新定义“战争电影”
诺兰的《敦刻尔克》既没有气势恢宏的战斗场面,也没有血肉横飞的暴力美学,几乎抽空了“战争电影”所赖以支撑的价值体系:“幸存”(survive)才是《敦刻尔克》真正的主题。《敦刻尔克》不再满足于讲一个引人入胜的“他人”的故事,而是要让观众全身心投入与剧中人物一起体验敦刻尔克撤退时的内心感受。《敦刻尔克》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片,但它遵循了商业电影的伦理诉求——“希望”。给影片中的幸存者,也是给观众以“希望”。
“战争电影”再一次被诺兰的《敦刻尔克》重新定义了。正如众多影评所发现的,诺兰几乎违背了“战争电影”的所有成规和经典范式。

电影《敦刻尔克》海报
从战士到幸存者
这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最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题材的电影,既没有气势恢宏的战斗场面,也没有血肉横飞的暴力美学,甚至连“拯救大兵”式的牺牲与正义也谈不上。片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主人公,主要角色中有竭力逃脱死亡阴影的年轻士兵,有先自救进而参与救援的民用船主,还有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片中人物也比较单薄,没有任何他们的个人信息,比如他们的家庭、爱好等等,以至于很多观众记不住他们的面孔和名字。他们的敌人德国纳粹自始至终没有展现,有的只是空中不时的轰炸、海中的鱼雷、不知来自何处的子弹以及高空盘旋的战机。如果没有字幕对相关背景的交待,我们甚至都无法与作为真实发生的敦刻尔克历史联系起来。这种对历史的主动疏离、对暴力的主动回避、对英雄主义的刻意虚化,使得诺兰的《敦刻尔克》几乎抽空了“战争电影”赖以支撑的价值体系:和平正义、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牺牲精神、团结互助……
正如诺兰所说,“幸存”(survive)才是《敦刻尔克》真正的主题。何为“幸存”?幸存即是“在某个有危险的事变之后仍然存在或生存”。“幸存者”首先是这一危险事变中的弱势一方,他们无力抗衡强敌,甚至都无法决定自己的生死。正如《敦刻尔克》电影中时不时冒出的一梭子子弹、时不时就俯冲而下的敌人战机一样,撤退中的联军士兵除了逃跑、俯卧、抱头下蹲之外,几乎无能为力。这种“生死由命,福贵在天”的绝望感,正是“幸存者”对命运不可知、不可控的真实写照。因此,即使是电影想要着力刻画“幸存”,但诺兰的策略也不是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凸显“经过奋力抗争之后,幸存者精神和人格的伟大崇高”,相反,诺兰所做的,不仅仅是让强敌退居幕后(只以射出来的子弹来代替),用逃避来替代反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电影中几乎抽空了“真实的历史场景”:空无一人的街区以废墟的方式存在,士兵身处其中成为“射击游戏”中的移动标靶;蜿蜒漫长的海滩以裸露的方式存在,士兵们除了等待登船之外几乎无事可做;浩瀚无垠的大海则更是显现出不稳定、随时可能埋没一切的方式存在,士兵们所能做的只有碰到危机时刻抱紧船舷或跳海逃亡。这种对死亡威胁对象的抽象化处理,使得诺兰的《敦刻尔克》由一部可以拍成纪实性的战争历史题材影片而一跃成为杂糅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的先锋电影。其所欲阐释的“幸存”,也不再只是二战中英法联军士兵的“幸存”,而是可以与新世纪以来的当代观众形成强烈精神共鸣的“幸存”。
代入与沉浸
诺兰的《敦刻尔克》又不是满足个人趣味、追求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虽然诺兰有意强化了“幸存”主题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但他仍然希望能够调动他所能够调动的电影叙事手段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敦刻尔克》不再满足于讲一个引人入胜的“他人”故事,而是要让观众全身心投入与剧中人物一起体验敦刻尔克撤退时的内心感受。观影时强烈的代入感不是《敦刻尔克》所独有,但大量运用主观视角却是该片比较突出的特点。片中海、陆、空三个空间密集的主观视角使观众恍惚在剧中。开场镜头随汤米躲开德军的子弹在法军帮助下从街角转到海滩时,自此转换为汤米的视点。空中模拟飞行员视角的镜头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据说诺兰这次是做减法,极简主义拍摄,追求真实拍摄,拒绝CG技术。但不得不说他在视点真实感的追求上确实是不遗余力的。与视点相对应的,还有景别。与一般战争题材影片中经常出现的大场面不同,《敦刻尔克》大量使用中近景甚至特写,大场景却不太多,而且大场景也多是剧中人物所看到的。观众对片中节奏强烈的配乐印象深刻,也是该片引发争议较多的,音乐几乎从头贯穿到尾,节奏密集,似乎永不停歇,从效果上看,音乐在营造情绪,强化观众现场感上起到了难以忽视的作用。
诺兰希望观众能“沉浸其中”,“欲罢不能”。为此,他学习默片,压缩台词,调动起观众视觉听觉多种感官。强烈的代入感和现场感确实带给观众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但诺兰对敦刻尔克撤退这一历史事件的想象限制了影片对人性探索的深度,似乎人在这种境况下只剩下了活着回家的念想。影片的色彩阴冷,光线黯淡,所营造的始终是让人焦虑、恐慌的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欢愉快乐的,而是处处碰壁、跌到低谷的绝望痛苦。所以片尾当观众随着防波堤上指挥官的视线看到无数小船出现在眼前,战士们欢呼一片的时候,压抑的情绪终于得到释放,如释重负。对独特观影体验的强烈追求带来的是与观众“战争大片”的预期相差甚远,也让熟悉诺兰电影招牌的观众出乎意料。
“希望”的悬念
在当代导演中,既熟悉主流观众的观影心理又擅长掌控观众的,诺兰毫无疑问是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电影上映前,诺兰在接受采访时就曾反复强调,《敦刻尔克》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片,而更像是一部悬疑惊悚片。但是,《敦刻尔克》正式上映之后,观众却发现,电影叙事既不烧脑,也不悬疑,似乎不像诺兰的风格。那么,如何理解诺兰所说的“悬疑惊悚”?是他在故弄私虚,还是另有所指?
根据真人真事和真实历史改编或创作的电影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评述一个尽人皆知已毫无秘密可言的故事?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二战中一次著名的军事行动,英军在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救出了33.5万人,这是史实。一部没看就知道结局的电影,在哪里设置悬念?设置一个怎样的悬念?
诺兰的选择是,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已无悬念”的真实历史场景中,突出和强化普通士兵个体的命运、个人的情感,并唤起观众对这些普通个体的生命关怀和命运关注。以撤退大军中一个年轻士兵和他的两个朋友为代表,用他们的生死牵动观众的内心。悬念之所以牵动观众的心,首先是观众对悬念事关人物的心理认同,对自己喜爱或同情的人物我们才会关心他的生死。在《敦刻尔克》的悬念生发机制中,这几位年轻士兵就像我们的家人、邻居和朋友,我们对年轻生命的珍惜足以触发全片悬念的开关。尽管我们都知道了故事的结局,我们仍然关心他们的命运。
那么,如何让这一悬念维持整部电影?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叙事不同,这部影片不再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路线来组织事件,而是开头就进入了危机的解决过程,全片107分钟一直到最后几分钟危机解除,故事也随之结束。格里菲斯“最后一分钟营救”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与“一分钟”的危机解决时间有很大关系。《敦刻尔克》则是开场就进入了危机,要维持107分钟的叙事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
一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幸存者”士兵自己。诺兰预设了一位普通的士兵汤米作为主人公,将他置于完全超出他个人所能了解和掌控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役”的场景之中。他不仅不是能够运筹帷幄的军中领袖;他甚至脱离了自己所属的部队成为一名“散兵游勇”。这一状态,使得汤米的命运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他的命运无疑是整个英法联军的缩影,但同时他又因此成为一个“自由人”,因此汤米才能在海滩上“四处游荡”,才能设法通过伪装蒙混登船,才能在成为数百万撤退部队的一名“旁观者”——通过他的眼睛,实现对整个军团从总司令到普通士兵的整体呈现。
另一方面,如果“幸存者”完全孤立无援,那也就真的变成存在主义和荒诞派戏剧了。《敦刻尔克》最终还是遵循了商业电影的伦理诉求——“希望”。《敦刻尔克》采取了三线并置的平行叙事的手法,从海陆空三方面展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全景”。但这一“全景”式的平行叙事手法,恰恰成为超越“幸存者”汤米这一单一叙事的重要机制。如果说以汤米为代表的普通士兵这一条线索是“能否幸存的悬念”的话,那么,法国民船和英军战机这两条线则展开的是“能否营救的悬念”和“能否战胜的悬念”。而正是后两条线,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给人以“希望”。民船的救援代表的是民心所向,是给整个敦刻尔克大撤退建立起了情感认同的基础。这条线索的叙事也经历了从船长与士兵之间从陌生到熟悉,到最终“站在同一条船上”并肩作战的过程。战机空战更是电影中唯一“正面迎战”的场景。战机在明知汽油不足以返航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与敌机周旋;在油尽滑翔的状态下最终消灭敌机,赢得了地面上从将领到士兵们的欢呼雀跃——这是整部电影唯一一次令人振奋的场景,也最终给整部非常沉闷、濒临绝望的电影涂抹上一丝亮色。飞行员滑翔着陆之后,冷静地烧毁了战机,微笑着被俘,成为战争题材电影英雄主义的呈现。
由此看来,电影中三线并行的叙事便不仅仅具有全景呈现、情节补充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调节“幸存”的压抑,给影片中的幸存者,也是给观众以“希望”。
理性思考战争
敦刻尔克,法国北部的狭小港口城市。在二战爆发初期,有40万的英法联军被德军发动的闪电战围困在这里。在三面被袭的绝望境况中,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从海上撤离三万人,但最终却在大量民用船只协助下实现了33.5万名士兵的成功撤离。影片《敦刻尔克》导演诺兰说,他并不把这部影片看作是战争的故事,而是求生的故事,关于求生的悬疑故事。他不想表达对战争的态度,究竟是反战抑或支持战争,他只想用平静的讲述方式将观众带入那场战场,身临其境般地感受被死亡感笼罩的人们的内心虚空和恐惧,以及由此而展现出来的真实生存状态、心理活动和行为。

影片《敦刻尔克》剧照
《敦刻尔克》在战争类影片中算是拍得非常克制的,没有宏大而激烈的战争场面,没有血腥的画面,没有英雄主义的凸显,有的是真切的代入感,让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在导演镜头下,被带入那个70多年前敦刻尔克海滩上。导演诺兰用画面、音符让人们去体验和感受战争,实现共鸣。虽然诺兰在采访中说他没有能力告诉观众“战争是什么”这样高度哲学化的问题,但是他确实做到了让我们在观影之后对“战争是什么”的问题进行长久而深刻的反思。
《敦刻尔克》是一部类似纪录片性质的电影,它无法被剧透,它不是能够用具体的语言来描述完备的电影。它从三个视角将战争拉到我们身边——堤坝上的一周、海边的一天、空中的一小时,三个时长不同、地点不同、人物不同的场景,在切换中将人们的情感拉向高潮。虽然《敦刻尔克》拍得节奏平缓,没有激烈冲突,没有高潮起伏,但是却在细节之处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例如一位陆军军官和一位海军军官正为如何撤离而焦灼不安时,海军军官拿起望远镜望向了大海,陆军军官问他看到了什么,海军军官从望远镜中看到的是无数的民间小船正在向敦刻尔克海滩驶来,此时他眼含泪水地慢慢吐出了一个词:home(祖国)。敦刻尔克离英国只隔了一道40英里宽的英吉利海峡,跨越了它就回到了祖国,可是即便近在咫尺的家园却让人有无法触摸的无奈。英国派出的救援驱逐舰总是被德军击沉,获救的希望燃起瞬间就被熄灭。然而没想到的是,向民间发出的号召居然得到了热烈响应,这种时候是最能感受到“祖国同胞”这四个字的意义。让人感动的场景是成功撤离回到祖国的士兵本以为会被当作逃兵而受到民众的鄙视和唾弃,然而他们受到的却是英雄般的礼遇,有人送毛毯,有人送啤酒和食物,他们依旧是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依旧被欢迎回家,不论胜利与否。因为活着本身也是一种胜利,只要活着就会有希望。
敦刻尔克大撤退不是一场值得大肆宣扬或者被歌颂的胜利,因为它是被迫的撤退,虽然成功撤退了33万多人,但如丘吉尔所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来获得胜利的。但这次撤退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却鼓舞了人民,在困境中自强和奋斗,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一直以来,战争片都不乏正能量的主题,人们在观看中情绪激昂。然而《敦刻尔克》以及去年上映的同样根据真实史实拍摄的《血战钢锯岭》从不同的视角让人们重新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究竟是胜利还是灾难。从这个角度讲,战争是场双输的游戏,而不是一场零和博弈。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即便盟军最终取得了二战的胜利,但自身亦元气大伤。扛枪上战场的兵士身后,有爱他们的父母,有等待他们归来的妻儿。有多少家庭把所有的儿子都先后送向了战场,期盼到的则是一个个噩耗。即便是战争结束后那些活下来的兵士,在战后的几十年中也依旧活在战争的阴霾下,许多人无法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战争结束了,生活继续,只是战争的影响却长久弥散。《敦刻尔克》再一次以独特的视角让历史细节重现,它启迪人们学会反思并时常反思,让那些动辄将发动战争看作儿童游戏一般的人认识到,战争不是游戏,因为参与其中的玩家都是注定的输家。如果这部影片能够让人们在观看后增进理性思考战争的智慧,就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手游经济不能透支未来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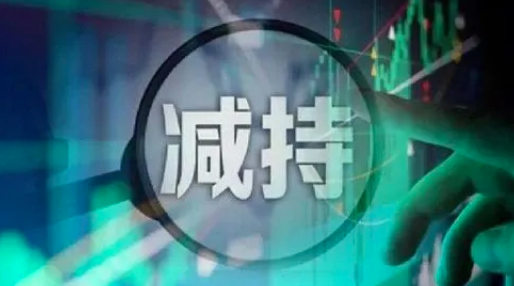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