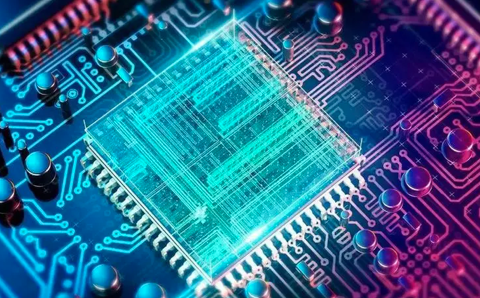庄子的反智主义
来源:中国金融新闻网 作者:司马朔 发布时间:2017-06-16
“早上懂得道,晚上死了也可以!”《论语 里仁》
孔子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心的人不会忧愁,有勇气的人不会害怕。”(《论语 子罕》)
这是孔子对智慧的崇拜,“知”(即“智”)与“仁”、“义”、“礼”、“信”一起,成为儒家所尊奉的人类基本价值系统。然而,庄子却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为防开箱、掏兜、撬柜之盗,人们一定会勒紧绳索,上好门锁,这便是世俗所说的智慧。然而大盗一来,却背起柜子、抬走箱子、拎起袋子而去,他们生怕绳索与锁钥不牢。那么以前所谓的聪明,难道不是为大盗聚财吗?(《胠箧》)
如果说这个故事只是说明小聪明不等于大智慧,庄子的推论则走得更远:
圣人出世而大盗蜂起,打倒圣人、释放强盗,天下才会太平……圣人不死,大盗就不会消失。虽然借重圣人治天下,却为盗跖带来更大利益。(《胠箧》)
如此结论真让人大跌眼镜:为何不责备大盗而要责备圣人?圣人怎么可能成为大盗之同党,一样地不可取?庄子的解释首先是认识论,而非价值论的:并非一开始就说圣人与大盗在价值观念上一样坏,想从他人那里得到不义之财;而是由于圣人总喜欢强调智慧与聪明,区别了智与愚,宣扬智慧,贬斥愚蠢,于是大大启发了众人:当有人想到要把自己的财富特别地看管好时,另一部分人也就几乎在同时想到如何把他人的东西不动声色地拿走。由于圣人从源头上开启了人的智慧——心思与聪明,打开了那个本不该打开的潘多拉匣子,于是人类社会就出现了偷盗现象,并自此难以禁绝。依庄子的预测:由于圣人的智慧启蒙,人类社会中在守财奴与大盗间所进行的这场护财VS盗财博弈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圣人并不会成为最终赢家。于是便有了如此的价值论判断:圣人乃人类智慧之第一因,始作俑者,故而他也像大盗那样可恨;护财之智并不能最终战胜盗财之智,智慧也就成为无益之物,就像偷盗之恶不值得人们尊崇一样。
河流干了,山谷便空旷;山岳平了,深渊就会填满。圣人死了,就不会有大盗,天下就太平无事了……所以拒绝圣人,放弃智慧,大盗就会消歇,扔掉珠玉之类宝物,小盗就没有了,烧了信符,砸了印章,百姓就质朴了;破了升斗,拆了量具,百姓就不再争斗。(《胠箧》)
庄子为我们提供的最“富有智慧”的终极解决方案是:将偷盗现象连根拔起,去除其始作俑者——圣人,放弃圣人对世人的最得意贡献——智慧。由于我们无法彻底去除坏的智慧,所以我们能做到的只有去除所有的智慧,去除智慧本身,因为那样的话,大盗也就质朴到想不起偷盗了。实际上,庄子对人类是否真正地拥有智慧、何为智慧以及智慧是否真的值得追求等,提出根本质疑。我们可以将他对人类智慧的整体性否定称之为“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并非庄子原创,而是其来有自:
拒绝圣人,放弃智慧,百姓将百倍地获利;拒绝仁,放弃义,百姓将恢复孝与慈爱;拒绝灵巧,放弃利益,便没有盗贼。(《道德经》第十九章)
人类放弃了对智慧的追求,便会根绝偷盗现象吗?很可能会是这样,因为那时人们将愚不可及,其智不胜任于盗;但也未必,因为偷盗现象起因极为复杂,非只聪明一端。我们可验之于动物界:偷盗实非人类的发明,动物界亦有之,有许多寄生性动物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取人之财而不向主人打招呼,在动物界并不罕见。这并非人类圣人教唆的结果,这说明智慧并非偷盗现象之必要条件,无智慧亦可有偷盗。放弃了智慧也许真的会没了偷盗,但同时也许会发生比偷盗更严重的后果。动物界为争夺有限生存资源而起的冲突,更多地不是通过较为和平的手段——偷盗,而是通过更为野蛮的手段——抢夺来解决。这说明即使我们自愿放弃智慧,根除偷盗,也无法因此而去除世上其他恶行,更严重的“不义”。智慧并非“不义”的唯一原因,放弃智慧不见得就会天下太平。
即使从人类文明的起点看,祖先们的直立行走、语言发明,理性能力(即智慧,“知”)萌芽,进而各式工具之发明,确实超出了,甚至是背离了原初的纯自然状态,不再属于自然人性;但自此而后,这种超原始状态的理性能力及其所有成果——文明或文化经长期积累,也已然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必然部分,成为人类再也无法脱离、去除的部分,成为人的第二自然。对已然进入文明时代(包括庄子所生活的时代)的人类而言,重新回到无知无识的原始时代,反而是极不可能,因而极不自然的事情。
放弃智慧之后的人类,除了没有偷盗(如果这是真的)现象,还会有什么发生,真会如老子所想象的“百姓将百倍地获利”吗?未必然。智慧(理性能力)乃人类在漫长、艰难生存斗争中进化出来的生存利器,它是中性的。诚然,人们可以用它来干坏事,比如偷盗;但也可以用它来做好事,比如用它来认识自然、发明工具,提高生产效果,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让更多的人减少艰辛,走出饥寒,等等。老子与庄子也许并未想到:当人类质朴到想不起偷盗时,可能同时也会愚蠢到无法认识自然规律、创造工具、改善自己的生活。比如我们的祖先会质朴到无力发明汉语。如果那样的话,老子也就无法用它来表达自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言,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之类的奇妙思想,庄子也无法用它来表达自己“拒绝圣人,放弃智慧,大盗就会消歇”之类的高明见解了。
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士多德)
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苏格拉底)
这是西方哲人的意见,他们鼓励人类努力获取更多的知识、更完善的智慧;可是老子与庄子却要我们更糊涂些才好,最好是糊涂到连做贼的心智也没有。如果可以重来,我们真得愿意为了一个“天下无贼”的宏愿,再回到那种彻底无知无识的原初状态吗?每个人均可扪心自问。
达尔文根据对动物界与人类原始部落的观察,就发现了伦理与法律秩序,即善恶之别,扬善惩恶信仰对于维护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他如此总结历史经验:
如果杀戮、抢劫、欺骗等公行,没有一个部落能维持在一起。因此,此类罪行总是在部落内部受到限制,并永远冠之以恶名。(达尔文:《人类的由来》)
相比于庄子的观察,显然达尔文的结论要更靠谱些。人类社会中确有善恶因果间存在错乱的情形,因而难免会动摇人们对善的信仰,甚至出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信条。然而,人类各民族文明史的经验证明:扬善惩恶才能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以善求福、远恶以避祸,方是人类社会之常态;善与福行、恶常招祸才是人生之大概率事件。因此,迷信伦理相对主义(因善恶因果联系之相对性导致对善的绝对失望,对恶的放肆追求)信念,进而崇拜以恶求福、互害互欺式的小聪明,实非致福持福之道。相反,以严谨的法治与自觉的善行谋求社会和谐、个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哲学理性、文明良知与人生智慧。
责任编辑:《每日财讯网》编辑
上一篇:《白鹿原》: “忠实困境”
下一篇:如何阅读经典?

〖免责申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其图片及内容版权仅归原所有者所有。如对该内容主张权益请来函或邮件告之,本网将迅速采取措施,否则与之相关的纠纷本网不承担任何责任。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海运费暴涨、“一舱难求”再...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桥水Q1疯狂扫货美股“六巨...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
光伏企业竞相布局 0BB技...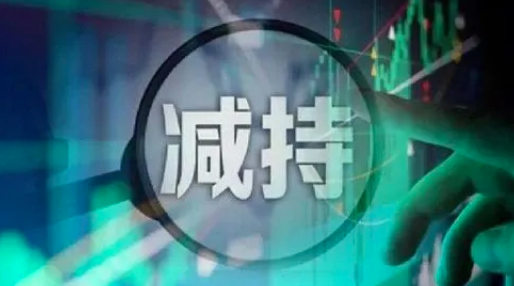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
A股突发减持潮来了!近20...